我们如何接近事物?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一般人并不经意如此愚拙的问题,但艺术家和思想家却是严肃地对待这种“愚拙”的人。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愚拙”,我今天来这里,想与各位艺术家讨论一位以一种愚拙的方式处理了这个愚拙的问题的思想家。这位思想家就是海德格尔,而这种方式就是现象学。

胡塞尔,1910年代
大家都知道,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原则是“面向实事本身”(或译“面向事情本身”),它被称为“一切原则中的原则”。它的意思说白了就差不多等于中文的“实事求是”。当然,在学理上,这个原则要复杂得多。对于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来说,我们只需指出这个原则的两层意思。
首先,这个原则包含着现象学的“无前提性”要求。胡塞尔认定一切旧哲学都是不严格的,因为旧哲学总是采取了“自然的思想态度”,后者包括如下“信念”或者“假设”:外部世界是实在的,精神和观念都是物质性的心理过程。在胡塞尔看来,这种自然的态度对日常生活以及科学研究是有效的,为了日常地生活,我们是需要这种“信念”或者“假设”的;但对严格的哲学来说,它却是不够的了。严格的哲学需要“反思的彻底性”,它不能有任何预设,不能以任何假定为前提,因为任何“预设”和“前提”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偏见”。毫无疑问,现象学的这个“无前提性要求”给现代思想带来了一股清醒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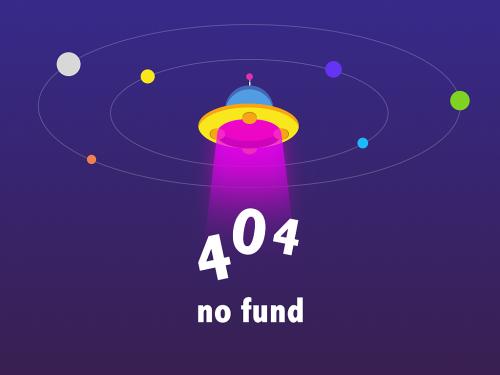
《弯道》
保罗·塞尚
纸本水彩、铅笔
49.2cm×31.7cm
1900
光达美术馆
其次,现象学原则包含着要恢复和激活人的原初生动的感受力的呼声。胡塞尔通过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悬搁”他所谓“自然的思想态度”,以确立哲学的严格起点:哲学只从“在直观中原本地呈现出来的东西”出发。胡塞尔这种对当下直观或感知的直接性的强调,本身也表露出现代人恢复生动的感觉力的要求。这里最要紧的当然是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方法。若以传统哲学观点看,“本质直观”一说在字面上就是不能成立的。“本质”如何可能“直观”?传统哲学认为,“本质”(观念、一般之物)之获得唯有通过“抽象”方法,或者是通过“普遍化”(generalisierung)形成等级性的概念(种、属、类),或者是通过“形式化”(formalisierung)获得形式范畴(如亚里士多德的十二范畴)。但胡塞尔却偏偏说,“本质”是通过“直观”获得的,有一种“观念直观的抽象”。
这对传统意识哲学来说当然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了。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试图在旧哲学的概念抽象的把握方式之外,寻找一种对现象、对事物和世界的新的把握方式,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胡塞尔之后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讲,胡塞尔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现象学原则,也就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思想的一个“共同口号”——“面向实事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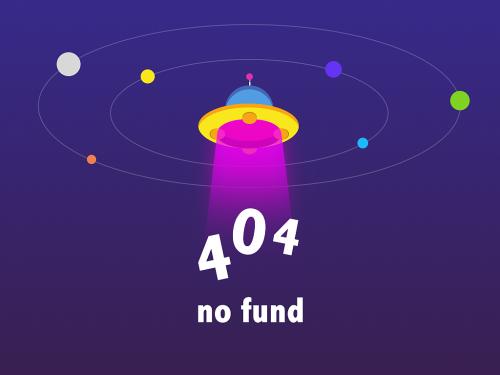
海德格尔的石瓦木屋,托特瑙山
我们接着来说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被公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两大哲学家之一,他从现象学出发开创了现代思想的新局面。胡塞尔现象学的“实事本身”是“意识以及意识的对象性”,他关心的是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但海德格尔却试图跳出意识哲学的范围,他把现象学的“实事本身”理解为“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之存在首先是事物(希腊文的cremata)的存在。于是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的首要关心是事物本身,是物的自在存在。于是问题就成为:如何达到物的自在存在?
物本身就是物的“自在”(ansich)。海德格尔还经常使用“自持”(insichruhen)一词来描写物的自在性质。所谓物的“自持”,是说物具有一种“内在安宁”,具有一种“安于自身”、“守住自己”的倾向。这就表明了我们接近物的困难。自在自持的物难以接近,因为物自身是“幽闭的”。现象学批评家斯塔罗宾斯基用“致密”一词来形容我们这里所说的物的“幽闭”性质,可谓适恰。在这方面,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说法是“阴沉”(das dumpfe,das unheimliche)。在《林中路》中,海德格尔曾讲到一块石头的“阴沉”:我们感到石头的沉重,但我们无法穿透它;即使我们砸碎石头,石头的碎块也决不会显示出任何内在的东西,因为石头碎块很快又隐回到同样的“阴沉”中了。[2]物的这种“阴沉”是莫名其妙的。我们下面也会看到,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艺术作品才能揭示物的这种“阴沉”、这种“自在自持”。这种“阴沉”是指向虚无幽暗之境的。也许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们才最有可能体会到物的这种阴森森的境界。

《静物》
乔治·莫兰迪
布面油画
35cm×40cm
1948
光达美术馆
不但物本身因为自在、自持、致密或阴沉的性质而难以接近,而且在人的心灵方面也有许多因素使我们无法接近事物本身。我们久已习惯的思想方法是“表象”(vorstellen)思维。要问:什么是“表象”呢?“表象”首先是把事物立为“对象”(gegenstand)。“对象”就是“对立之象”。这在态度上首先就出了问题:“表象”是一种与事物相对而立的“敌视”态度。其次,“表象”是“对而象之”,是对事物的一种“观念化”的把握。人们认为个别事物表现出来的样子(现象)是不可靠的,虚假的,关键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作为“本质”的“象”(idea,eidos)才是绝对可靠的,才是真实之物;这个“本质”不在事物中,而在我们通过“普遍化”方法形成的观念(概念)序列中。所以“表象”思维是一种“概念抽象”思维。最后,在“表象”思维基础上的哲学和科学已经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概念机制,影响并决定着我们对待事物的方式,构成我们与事物之间的一道屏障,蒙蔽了事物的自在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套概念把握方式不但不能让我们接近事物,而且还构成对自在自持的事物的“扰乱”。
横在现代人与事物之间的屏障越来越厚重。我们多半已经无法直接接近事物了。因此,恢复事物的自在自持的存在,已经成为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的一个共同要求。现象学,特别是经过海德格尔发展的现象学,乃是这个要求的最集中表达。以另一位现象学批评家阿·贝甘的说法,就是要恢复事物的“纯洁性”,恢复“惊奇的观照和事物最初在场的完整性”。[3]

《阅读中的迭亚戈》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纸本蓝色圆珠笔
22cm×13.3cm
1952
光达美术馆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本身呢?海德格尔首先做的是一种“用具(器具)”(zeug)分析。人们一般会从用途角度考察一个用具,认为用具的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中。这当然没错,但却是不够的。海德格尔的想法比较奇怪。他认为,我们对用具有着一种在先的“信赖”,因为我们在使用用具之前总是已经“确信”,用具作为某种可用的东西随时可供我们使用了。这种“信赖”后来又被叫做“可靠性”。“有用性”本身是以“可靠性”(verlasslichkeit)为根基的。为什么我们脱鞋、穿鞋,毫不经意,从不思量?是因为有“可靠性”。我们用某个用具前,总是已经依靠着、信赖着它了。“可靠性”与“有用性”的关系,具体如家俱,抽象一点如“家”,都可供说明。“家”是我们用得最多的地方,而“家”首先是可靠,可依可赖。我在家里,黑灯瞎火都能摸到家俱,走进家里的每一房间,这就是“在家”的感觉,这就是“可靠性”了。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可靠性”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的认为是作为“境域”(horizont)的“世界”。显然他的思路在此作了一种跳跃。他是从用具的“因缘性”角度入思的。世上任何用具都不是孤立的,而总是“相互指引”的,总是有“因缘”的。举例说来:锤子与锤打有缘,锤打又与修固有缘,修固又与房屋有缘,房屋又是为我们人的某种存在可能性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因缘联系”实际上就构成我们生活的“境域”。用具是在作为“因缘联系”的世界境域中与我们照面的。因此,我们对用具的“信赖”的依据并不在器物本身,而是在作为“境域”的世界。世界境域为事物备好了这样一种使用方面的可靠性,使我们能够信赖之,能够在与事物的交道中自由地活动。

《安妮的大衣》
阿维格多·阿利卡
布面油画
116cm×89cm
1973
光达美术馆
只有在作为“有用性”之根基的“可靠性”中,也就是说,只有在世界境域中,才能发现用具的真实存在。但这种“可靠性”不是日常的目光或传统哲学的目光所能发现的。对一双鞋的实物及其使用过程的观察,是发现不了“可靠性”的。“有用性”(用途)很具体,是可“知”的;而“可靠性”却差不多是虚无缥渺的,指向一个意义境域(世界),是在一个意义境域中才能显现出来的,是不可“知”的。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通过艺术作品,用具的“可靠性”才被启示出来,聚集在这个用具上的意义境域才被开启出来。已经脍炙人口的关于凡·高的农鞋画的经典描绘,以及另一段同样诗情洋溢的关于希腊神庙的描写文字,都是海德格尔对由艺术作品启示出来的意义境域的思想经验。
海德格尔在此形成一个十分关键的思想:不仅用具的存在要通过艺术作品才能得到体验,而且扩大而言,一般物之存在也须借助于作品才能够为我们所体验。这个断言就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了。它几乎与康德哲学一脉相承:“物本身”是不可“知”的。然而现在,在海德格尔看来,不可“知”并非不可“接近”,我们仍然可以借助于艺术作品去“接近”物本身。
为什么要借助于艺术作品才能认识物的自持存在呢?我们仍然必须联系到前面讲的海德格尔关于“世界境域”的思想。事物的自在存在是在世界境域中显现出来的。这个世界是显-隐二重性的发生,即“天空”与“大地”两大世界区域的“紧张的和谐”运动。艺术作品正是对世界境域的开启和确立。海德格尔说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天空”(himmel)与“大地”(erde)作为两个相对的世界区域,可以说世界的两种运动方式,用海氏的话来说,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方式。海氏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真理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为“天空”与“大地”的“争执”。而艺术创作就是让作为“天地之争”的真理在“形象”(gestalt)中“固定”下来。在作品中实现的世界境域的运动(或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同时也正是物之自在存在的开启。

《穿斗篷的迭亚戈》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青铜雕塑
38.1cm×34.5cm×22.3cm
1954
光达美术馆
海德格尔这种对艺术和艺术作品的理解是别出心裁的,需要我们在当下艺术实践中加以体会和检验。就对物之自在存在的非主体主义理解而言,海德格尔上述思想包含着一个关键的新洞见:事物的自在存在并不是从我们的主观活动性中获得其意义的,而是从“世界”的发生运动中获得其意义的。任何一种显现都是在“天-地”两大世界区域中进行的。这两大区域的既显又隐、既对抗又共属的交互运动,乃是事物自在自持的存在的依据。
上面我们看到,海德格尔的艺术思考已经达到这样一点:“物”乃天地之间一“造化”,而“天地之争”由“作品”固定下来。所以,我们只有借助于“作品”才能够认识物的“自在存在”。但除了艺术的道路之外,海德格尔后来认为还有另外一条接近物的自在存在的道路,那就是“思想”的道路。
这种“思想”被叫做“思念之思”,也被称为“审慎之思”。它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更不是哲学和科学意义上的“表象”思维。海德格尔赋予它某种玄怪的特性。大致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思想”,一种非对象性、非客观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包含着以下两个要求:“向着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所谓“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简单说来就是let be,让事物如其所是地存在,让事物“安于自身”,不要总是一上来就把事物“对而象之”,急匆匆忙不迭地占有之、开发之、利用之;而所谓“虚怀敞开”(offenheit),则是一种对神秘的敞开接纳的态度,就是要重新唤起一种对神秘的期待和敬畏的心情,要对天地人间有一种空无幽远的思绪。以我们的理解,这种解脱了主体性的“思念之思”仍然具有现象学的意义,它实质上就是现象学的“让显现”意义上的“思想”。

《风景》
乔治·莫兰迪
布面油画
38cm×55cm
1940
光达美术馆
以这种“思念之思”,我们才可能接近自在自持的物。我们且来看看海德格尔给出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他对一把壶的“思想”。如若从科学上来研究,壶不过是一个由泥土制成的器皿而已,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均可得到精确测定。但海德格尔以为,科学却不逮于壶的本性。海氏为我们端出了如下思法:壶之为壶是什么呢?壶之为壶是能够容纳,但能容纳的不是壶的底和壁,而是壶的“空洞”,可见其实是“空无”构成了壶的本性。若再想下去,空洞的壶的容纳是为了倒出什么,也就是为了有所馈赠。壶馈赠饮料、水、酒。水、酒乃天地之造化,既可解渴、欢宴,又可敬神、献祭。因此,壶之本质乃是集“天、地、神、人”于一体。
物的本质是对“天、地、神、人”的聚集。我们看到,晚年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法当然是十分玄妙的、诗意的。与“作诗”一样,这种“思想”仍然可以理解为对物的“阴沉”的突破,对物的虚空幽暗之境的穿透。而且,海德格尔在这里仍旧是从世界境域发生的角度来理解物的自在存在。不过,海德格尔这时的“世界”观已有所改变,“世界”已不再是“天”、“地”两维,而是由“天、地、神、人”这样“四方”构成的整体。所谓“世界”就是天、地、神、人“四方”的游戏运动。只有从“世界游戏”运动的角度来“思想”,我们才能接近自在自持的物。
海德格尔曾经设问:是否每一种思与言都是客观化或对象化的?这里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是如何可能的?这是一个现象学的问题。根据现象学的原则,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表达为:如何接近事物的自在自持的存在?海德格尔一生尝试了多种途径来解答这个问题,旨在纠科学技术思维之偏,究问天地世界人生的本来面目。

《二十四诗品之劲健》
司徒立
布面油画
150cm×250cm
2010-2011
光达美术馆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海德格尔为我们给出一个玄妙的答案:只有通过“诗”(艺术)和“思”(思想),而且是后主体主义的“诗”与“思”,而且是处于近邻关系中的“诗”与“思”(所谓“诗思合一”),我们才能在“世界境域”中,才能在“天”之开启与“地”之幽闭的发生运动中接近自在自持的事物。天玄地黄。万物在天地之间生成。人也在天地之间生成。历史、文化也在天地之间生成。天地“之间”是“世界”。唯在“世界”运动中才有物的自行呈现。而人群中间,唯有从事艺术的人和从事思想的人才能超越私人境域(私人世界)而进入天地之间的共同境域(世界),去接近自在自持的事物,去揭示事物的真相。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把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引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上,其基本宗旨是寻求以非形而上学和非主体主义的思想姿态去面对今天这个技术世界。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方式表达了恢复事物的自在存在的努力,并且以自己的思想实践倡导了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这种思想当然是与旧哲学和科学思维格格不入的,但它业已在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中产生的普遍效应却让我们相信:思想之虔诚就是一种坚韧不拨的力量。
[1] 本文系作者1998年12月28日晚在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杭州)作的报告,1999 年1月22日在南京大学哲学系重做一次(内容有扩充)。发表时作了删节。
[2] 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美茵法兰克福1994年,第33页。
[3] 参看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南昌1993年,第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