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导览】“物之华”展览前言及随想

物之华
兰友利
“物之华”这一展览形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西方静物画与中国古代宋瓷为主体的器物并列在一起,以画观物,以物映画,在二者的相互沟通之中产生出的微妙交融。宋瓷作为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发展的高峰,与宋画一起缔造出中国艺术的伟大时期。西方静物画作为一个古老画种,则体现出画家从观物进而理解世界的过程。

《水果静物》
安德烈·德朗
布面油画
35.6cm×40.9cm
1932
光达美术馆
将绘画与器物连接在一起,是因一个共通的主题而被等同观照,这个主题即是“物”。绘画被认知为艺术,但也是一种物;器物被认知为物,但也是一种艺术。器物作为礼的承载,在源初意义上即是祭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邓椿在《画继·论远》中说道:“礼者,人之极也。画者,文之极也。”礼必形之于供奉之物,画则离不开作品之物。子曰:不学礼,无以立。是以,礼构筑起“人之极”,礼器则是人之极的一种显现形式。绘画作为“文”的究极载体,也是一种供奉之物。在这个意义上,绘画与器物均不指向日常实用。二者则因这一隐藏的“物性”被共同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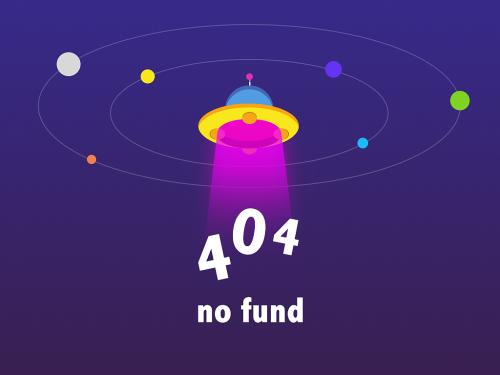
左:《静物》乔治·莫兰迪 布面油画
35cm×40cm 1948 光达美术馆
右:磁州窑乌金釉嘟噜瓶 金代 14cm×11cm
这一隐藏的“物性”并不是通俗观念中的物质性,而是“物之华”。“物之华”如果从唐代王勃“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一句中的含义,则是作为万物之精华理解。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这里的“物之华”则是与“物之实”相对立的概念。物之华与物之实为一体两面,空有华而无实,则无内涵。只有实而无华,事物则无从显现。朴实无华则是一种无华之现。无华之华是物呈现自身的最高显现形式。

《红石榴》
司徒立
布面油画
146cm×97cm
2001
光达美术馆
无华为事物的静寂之音,叩物之声而物自鸣。所以不是外界强加于物的声音,而是物自身之音。它的特性是沉默。可道之道,非常道;以华为华,非真华。无华与浮华造成了事物显现的真假维度,前者处于隐匿状态,但却持续在解蔽中,后者作为彰显,却成为真正的遮蔽。

《文件夹与盒子》
阿维格多·阿利卡
布面油画
33cm×41cm
1978
光达美术馆
无华之华回归到物的先天物性,犹如老子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在天地之前,这一物已然存在。在万物生成之后,这一物也并没有消失,它就在那里。亦如康德所说的“物自体”,它必须有,但却不可知。一旦名之,物就显现,因为语词破碎处,无物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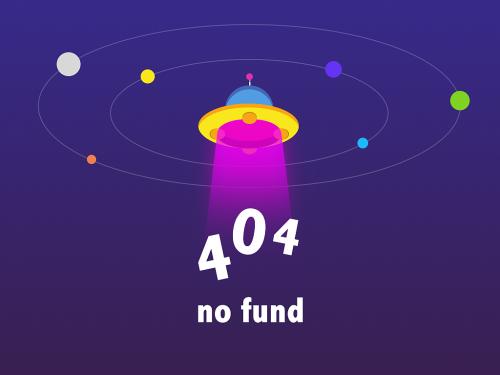
越窑秘色花口大碗
8.5cm×22cm
五代
海德格尔关于“物性”有一个非常经典性的揭示,那就是“斧成石亡” 与“庙成石显”的描述。石头被制作成了斧子,因其有用性而丧失了石头的物性。石头被建造成神庙,其物性反而因仪式感得以被强化。“物之华”作为物性绽出自身的方式,恰恰是在规避盲目使用当中显现而出。尤其是在物质被机械化批量生产的时代,那虽远尤近,唯一无二,无法被复制的“物之灵光”逐渐隐退,将绘画与器物重新连接在一起,可以看成是对“物之华”的再次召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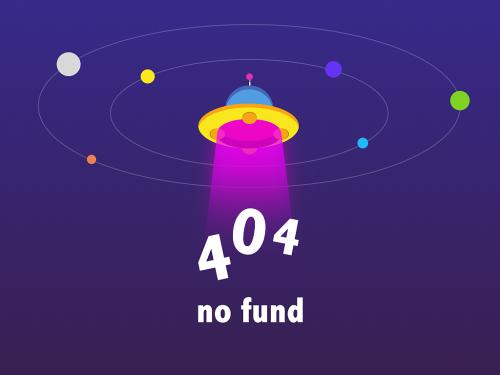
磁州窑黑釉白线条水注
7.5cm×8.3cm
北宋
物之华展览之随想
韦九谷
与司徒老师巧遇的机缘,如同此次展览,似有十分同趣的境缘。司徒深耕艺术沃田,于山之巅以观沧海,而我沉浸于中国古代美术的寻觅,孜孜不倦,这样的一种会合,令人非常有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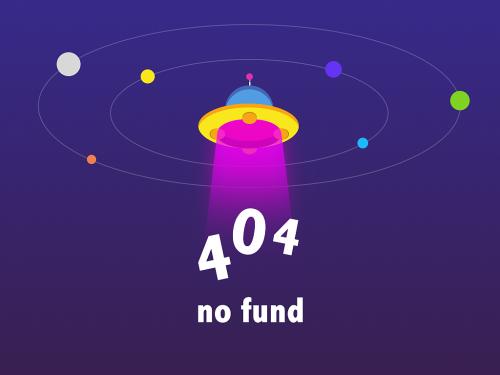
左:《静物》乔治·莫兰迪 布面油画
34cm×40cm 1956 光达美术馆
右:龙泉窑纸槌瓶 南宋 13cm×6.5cm
较早前,我也常以东西方诸艺术之比较自许,而后渐渐觉得诸艺术并不可以东西方简论之。其实很早以前即是全球化的地球村景象,诸艺术以超乎想象的交融弥漫在历史长河之中。此次由光达美术馆与我提供的不同形态的“物”,以某个点或者某个角度来呈现或诠释,是探研作品存在的一种崭新方式,深以为有趣。

《盘中葡萄》
亨利·方丹-拉图尔
布面油画
29.5cm×43cm
1886
光达美术馆
古代中国物之华者,大率归属于统治阶级,然而技术和生产智慧,皆来自长久的延续积累。此“华”当理解为“精粹”。朴实无华的哲学意义,属于精粹作品的构成内涵。在以理学为主导的情形下,追求朴素的自然之道,不仅两宋,实乃人类长久之诉求,恒久未变,物的外延表现,如书法、音乐、绘画,全然为情绪与感官服务。作者内心妙想表达“物”,观者以“物”感知到此种妙想,这便是作与受的关系。历史上精于道者,无不善于心灵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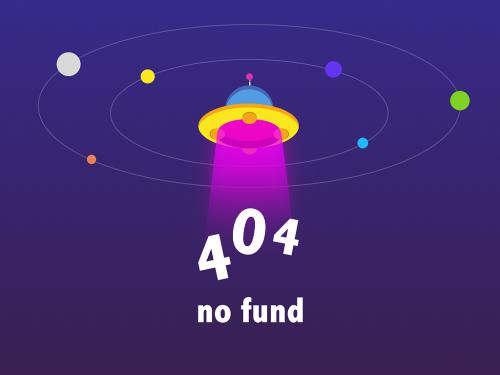
《小玫瑰》
亨利·方丹-拉图尔
板上布面油画
38.1cm×25.7cm
1875
光达美术馆
作品已然沉默,然而其物之华,熠熠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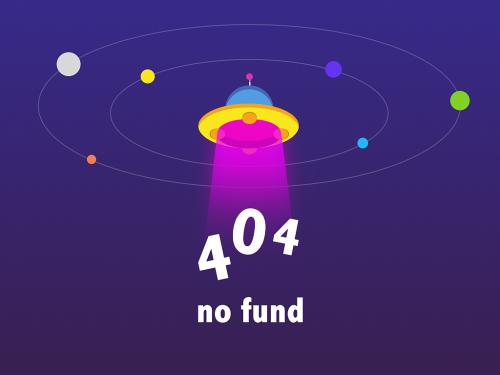
湖田窑青白釉梅瓶
36cm×19cm
北宋
愿同行学者,透过这样一种观看,可以内视人类之天性,在华而不实的浮世中,有片刻之肃静,走进一种实而不华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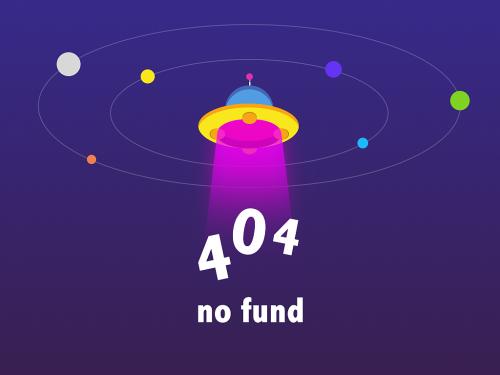
《罂粟花》
皮埃尔·博纳尔
布面油画
70.5cm×58cm
1914-1915
光达美术馆
